杂技从“小滑稽”到“活化石”
戴着圆帽和黑框眼镜,鼻子上顶着红色的小球,吴卫民的微信头像一直是他自己的“小丑”大头照,个性签名一栏写着“I,Acrobat”(我,杂技演员)。一张照片,一句签名,足以概括这位74岁老人的一生。
“吴老当之无愧。”当吴卫民的名字出现在新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时,武汉杂技厅的老同事们一点都不意外。从5岁第一次登台,到退休后仍在训练室盯着学生训练,吴卫民70年的杂技生涯不仅创演了数不胜数的经典杂技、滑稽节目,还培养了五代徒弟,这30多名学生均走上舞台,成了专业的杂技演员。
在非遗日前夕,长江日报记者走近这位被后辈们称作杂技界“活化石”的艺术家,看他如何用生命演绎杂技的苦与乐,又如何在新时代守护这门古老技艺的薪火。
从“小滑稽”到“活化石”
“摔了怎么办?摔了再来!杂技演员哪能怕摔。”吴卫民回忆起初学杂技时的情景,语气云淡风轻,面上还带着微笑。1951年,出生于杂技世家的他,外公是杂技团的副团长,父母是团里的演员和乐手,从小在后台摸爬滚打,跟着这位老师学学倒立,跟着那个演员学学翻跟头,身边可谓是“高手”环绕。
有一天,团里的滑稽演员陈老师心血来潮给吴卫民化了个滑稽妆,再把他抱到舞台上,说:“来,今天跟我上去演滑稽节目。”这是吴卫民第一次登台演出,彼时还只有5岁的他懵懵懂懂,却毫不怯场,在舞台上积极配合陈老师的表演,将台下观众逗得哈哈大笑。从此,吴卫民的“小滑稽”称号开始逐步叫响。
“那时候没有训练垫,都是直接在水泥地上练,脸上蹭掉皮是常事。”吴卫民摸着脸颊回忆,他小时候最怕在夏季和冬季练功,冬天冷得直打摆,上来就被老师要求倒立半小时;夏天一动就汗流浃背,没练一会儿衣服就湿得能滴水。“老师说‘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’,到了春秋,我问老师我们该休息了吧,老师又说春秋是最好练功的时候。”吴卫民说,当时他心里委屈又不敢反抗,经常一边默默流泪一边练功。
也是在这样的锤炼中,吴卫民练就了《大跳板》《空中飞人》等经典节目,成为当时广为人知的“小滑稽”。1964年中法建交,13岁的他随团赴法国演出。1967年,16岁的他登上天安门城楼,为外宾表演杂技。他的青春与新中国杂技的辉煌同步绽放。后来,吴卫民曾随团赴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冰岛等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演出,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和中国杂协“德艺双馨”荣誉称号。
荣耀背后是伤痛。“腰摔过、胳膊断过,杂技演员没几个‘全乎’的。”55岁那年,吴卫民退休后被返聘回武汉杂技厅教学。退休前,作为表演队队长,吴卫民带队到处演出的同时,也要承担选人和教学工作。退休后,他则将所有心思投入教学。几十年来,他带过五代30多名学生,有的已从杂技演员的岗位上光荣退休,有的和吴卫民一样从事着杂技教学工作,最年轻的一批则还留在舞台上。
严厉背后是沉重责任
在武汉杂技厅,吴卫民是传奇一般的存在,晚辈们在私下称他为杂技界的“活化石”。他一走进杂技厅大门,遇到的每位工作人员都会亲切地招呼他:“吴老师,您来了”,
武颖今年51岁,是武汉杂技厅的老师,也是吴卫民的第一代学生,跟他做同事的时间比做师徒还长,但直到现在,武颖看到吴卫民仍会想起自己小时候看到他就绕道走的事。“吴老师盯我们练功和排练的时候很严肃,那时候年纪小,就很害怕。”武颖说,等她也做了老师之后,才明白吴老师严厉的背后是沉重责任,“练杂技稍有不慎就有危险,面对一帮不懂事的小孩,不耳提面命怎么让他们集中注意力?”
30岁的王炼是吴卫民的第五代学生,目前早已是武汉杂技厅的“角儿”,还是多个杂技节目的主演。他回忆,自己第一次脱离安全绳练空中转体360度时十分紧张,果不其然摔了,吴老师很生气,大声吼了他,结果第二次尝试时就成功了。“吴老师就是我们心中的定海神针,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很安心,哪怕是骂我,心里也很踏实。”王炼说。
23岁的梁硕是东北人,是第五代学生里年纪较小的,从13岁开始跟着吴卫民学杂技。刚开始练功时,因为基础薄弱,他做动作经常达不到要求,重复多次后便会气馁,越做越不在状态,但每次都会被老师及时逮住。“谁懈怠或是想偷懒,我立马就能发现,然后吓唬他说要单独罚他做200个,他状态立马就好了,我还能不了解这群小鬼?”吴卫民得意地说,杂技演员没有不偷懒的,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过来的。
“严厉归严厉,但吴老师又厉害又负责,我们都很崇拜他。”梁硕记得有一次吴老师发现他有些松懈后,将他拉到一旁皱着眉头叮嘱他,杂技表演是一项团队工作,“不在状态”是很危险的,不仅会让自己受伤,还会连累队友。“信任很重要,信任老师,不辜负队友的信任,这些是吴老师教会我的,受用终生。”梁硕说。
学生练功时,吴卫民悉心教导,时刻紧盯;学生参加比赛时,他也全程跟随,寸步不离。第一次上台表演、第一次比赛,吴卫民都陪在学生旁边。这间挂着“刻苦训练,备战全国展演”的训练室里,承载着吴卫民最深的牵挂,他的学生们和杂技技艺的传承。去年,吴卫民因照顾病中妻子暂别教学,但他说:“等爱人身体康复了,只要团里需要,我随时回来,我有这份责任。”
(长江日报记者樊友寒)
【编辑:符樱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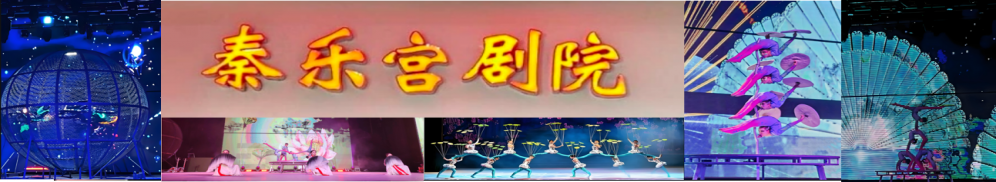
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500
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4500